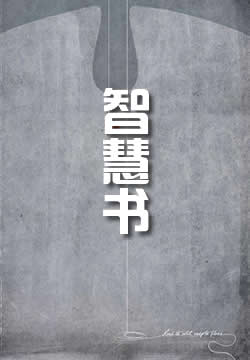柳河东集
作者:柳宗元章节列表
升序↑- 卷一·雅诗歌曲
- 卷二·古赋
- 卷三·论
- 卷四·议辩
- 卷五·古圣贤碑
- 卷六·释教碑
- 卷七·释教碑铭
- 卷八·行状
- 卷九·表铭碣诔 唐丞相
- 卷十·志
- 卷十一·志谒诔
- 卷十二·表志
- 卷十三·志
- 卷十四·对
- 卷十五·问答
- 卷十六·说
- 卷十七·传
- 卷十八·骚
- 卷十九·吊赞箴戒
- 卷二十·铭杂题
- 卷二十一·题序
- 卷二十二·序
- 卷二十三·序别
- 卷二十四·序
- 卷二十五·序隐遁道儒释
- 卷二十六·记官署
- 卷二十七·记亭池
- 卷二十八·记祠庙
- 卷二十九·记山水
- 卷三十·书明谤责躬
- 卷三十一·书
- 卷三十二·书
- 卷三十三·书
- 卷三十四·书
- 卷三十五·启
- 卷三十六·启
- 卷三十七·表庆贺
- 卷三十八·表
- 卷三十九·奏状
- 卷四十·祭文
- 卷四十一·祭文
- 卷四十二·古今诗
- 卷四十三·古今诗
- 卷四十四·非国语上
- 卷四十五·非国语下 狐
- 外集卷上·赋文志
- 外集卷下·表启
- 外集·补遗
- 附录
猜你喜欢的书
智慧书(中英双语)
《智慧书》是17世纪西班牙著名哲学家、思想家巴尔塔沙•葛拉西安的著作,自1647年问世以来,深受读者推崇,与《君王论》《孙子兵法》一起被誉为“人类思想史上伟大的三部奇书”。此书汇集了300余则绝妙的处世箴言,论及识人观事、慎断是非、修炼自我、防范邪恶等智慧与谋略。这些宝贵箴言历经数百年仍煜煜生辉。其文字言简意赅,对人性剖析深刻,在谈论道德问题方面更是极为精妙,显示出葛拉西安超越时代的智慧。它以一种令人感到惊异的冷峻、客观的态度,极深刻地描述了人生的处世经验,为读者提供了战胜生活中的尴尬、困顿与邪恶的种种妙策。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人生格言,人们不仅获得了克服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逆境的良方,更能增强对生活的理解和洞察力。《智慧书》是为每一个人而写,它深刻地描述了人生的处世经验.为读者提供了战胜艰险、提升自我的良策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说:“这是一本随时都能用上的书,是一位终身伴侣。在人类的处世哲学书中,此书是绝对的独一无二。”
类聚方
方剂学著作。1卷。日本·吉益为则(公言、东洞先生)著。成书于1762年。本书为方剂著作。选录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二书中的方剂220余方,依类编次。每方之后均广集原书各篇中应用该方的辨证立法,并有作者的考证,附以扼要的按语。现有《皇汉医学丛书》本。1955~195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亦有出版。
神仙可学论
唐吴筠撰。道教经书。收入其《宗玄先生文集》卷中。论述可用积学的方式成为神仙。在对神仙的看法上,本文不赞成嵇康的观点,而是认为神仙或是秉受异气而生,或是后天积学而成,集中论述如何通过后天的努力成为神仙。列举远于仙道的七种行为:以死亡为真,以生成为幻;认为仙必有限;强以存亡为一体,期待转生来世;陷于嗜欲,无法自拔;慕道之名,未得其实;养生莫究其本,务之于末;身栖道流,心溺尘境。近于仙道者亦有七种表现:情忘嗜好,不求荣显,以无为为事;刻志尚行,弃荣华、捐声色;忠贞奉上,仁义临下,恶杀好生;安贫乐道,以摄生为务;静以安身,和以保神;追悔以往,洗心自新;至孝至贞,至义至廉。论学仙之道时兼顾形神有无,颇周全。神仙可否学致的问题,自汉代以来即在道教中占有重要地位,本书对此作了一个总结。书中首先提出是否有神仙的问题,认为神仙不死“理无不存”,既有神仙则神仙可学。说成仙有不因修炼而致者,有必待学而后成者,有学而不得者,不能一概而论。又指出远于仙道和近于仙道的各七种情形,认为学仙道就是要“放彼七远,取此七近”。其结论为“神仙可学,炳炳如此,凡百君子胡不勉之哉!”实为宣扬道教神仙学之作。收入《正统道藏》太玄部。
雷峰塔
传奇剧本。清方成培著。作者《自序》说:此剧为“更定”他作而成,“遣词命意,颇极经营,务使有裨世道,以归于雅正。”近人吴梅《霜厓曲跋》说:“观其《自序》,煞费苦心。然剧中篇幅过狭,套数失次,亦非尽美之作。”日本青木正儿《中国近世戏曲史》说:“今《水斗》、《断桥》二出,最流行歌场中,艳丽之中,鬼气逼人,别具一种风格,亦杰构之一也。”此剧是一部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著名悲剧。作品成功地描写了白娘子为了争取自由爱情而进行的反抗斗争,客观地反映了以法海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仇视和镇压,具有反封建的重大主题。剧本人物形象鲜明生动,具有悲壮的悲剧美感和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。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宿命论观点和妥协思想。
明史通俗演义
《历代通俗演义》之一。共有一百回,自平民皇帝朱元璋开国,终至明思宗殉国,经历276年。朱元璋应运而兴,不数年即驱逐元帝,统一华夏,好不容易将当时的外族赶出中土,却又怕不断的骚扰,只好将长城筑高筑厚。也唯有此时,出现一位七次下西洋的郑和,带着当时的最高科技,庞大船队大大宣扬明帝国的势力。全书文笔流畅,故事生动。
唐梵两语双注集
亦称《梵汉两语对注集》。梵汉词典。唐天竺僧怛多蘖多、波罗瞿那弥舍沙合撰。一卷。专门收录汉译佛典中的音译名词。全书共收音译汉字七百个,下注梵语读音,但未标梵文原文。编排体例与《梵语杂名》基本相同。此书在国内久已失传。后传入日本,见录于唐咸通六年(865)日本求法僧宗睿的《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》。现见载于日本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四册。